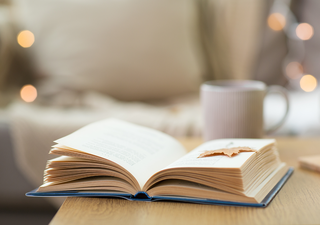擁有穩健堅實的實體經濟,是我國具有長遠競爭力的關鍵所在。
2020年10月26-29日,十九屆五中全會為“十四五”時期我國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做出了重要部署:“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,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、質量強國、網絡強國、數字中國,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、產業鏈現代化,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……”,這是黨中央立足全局、面向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,意義深遠而重大。
作為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,“十四五”傳遞出的信息量值得深入回味。新時期,為何把實體經濟擺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?
其實早在“十三五”時期,中央圍繞實體經濟發展就作了多次重要部署,無論是強調“著力振興實體經濟”“夯實實體經濟根基”,還是提出“堅持把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作為主攻方向”,底層邏輯均沒有脫離開“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”。
我國是靠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的,注定也要依靠實體經濟走向新的未來。
《中外管理》采訪的眾多一線投資者,產業專家,都表達了近乎一致的看法:“十四五”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。在這個特殊歷史時期,大力發展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,有助于我國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,掌握發展主動權,塑造國際競爭優勢。其中,數字化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助推力;戰略性新興產業,代表著未來產業變革的新方向。
在“十四五”新一輪造富浪潮下,如何抓住實體經濟可能造就的機會點,前瞻性地展開布局?
1、“十四五”,從更宏大歷史維度審視實體制造業
當前,我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,即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現代化建設兩段征程的歷史交匯點,這意味著,“十四五”規劃天然就帶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使命。
在這一關鍵節點,國家為何重點圍繞實體經濟做規劃部署?
達泰資本創始管理合伙人葉衛剛分析認為:國家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把實體經濟擺在一個戰略性高度,是看到了西方國家過去10-20年間走過的“脫實向虛”的彎路。
“以美國為例,過去4年,美國經濟為什么被特朗普折騰得這么厲害?主要因為美國‘脫實向虛’太嚴重了。過去20年間,美國基本上把大量實體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外包出去了,這導致美國經濟的‘空心化’,制造業和農業都不景氣、失業率大增,至少一半民眾的獲得感不足,政局也不穩定。除了美國,英、德、法等西歐國家也有類似問題。”
事實上,中國也同樣走過一段“脫實向虛”的彎路。過去5-10年間,大量熱錢涌向“模式創新”,電商、互聯網、網紅經濟等大行其道。但客觀評判,虛擬經濟對于中國總體實力的提升,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。
對此,創客共贏基金創始合伙人李建軍表示認同。
他告訴《中外管理》:近幾年實體經濟的受重視程度,確實不如虛擬經濟。所以,“十四五”時期,中央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做調整規劃是必然的。近期四大金融監管部門約談螞蟻金服就可以看出,國家加大對金融反壟斷的監管,就是一次對虛擬經濟重新定義的過程。
“經過這次疫情,以及美國對華貿易制裁后會發現,是實體經濟在支撐國家的發展,實體經濟才是社會財富和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。尤其是制造業,對穩定就業、改善民生,以及維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。而且,當一國外部受到沖擊時,國內實體經濟穩定就會很安全。”李建軍分析:“但過度傾向虛擬經濟,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。比如過度使用金融工具創新、信用評級,容易讓企業鉆貨幣政策監管放松的空子,將引發極高的風險。”
“總之,我們要把實體經濟發展放在更宏大的歷史維度上去把握。”賽迪智庫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如是總結道。
他認為: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,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國際格局的演變,各國圍繞實體經濟的競爭更加激烈——發達國家加快推進再工業化、新興國家加速快工業化,我國產業體系面臨著兩端擠壓的挑戰。而制造業,是大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、爭奪產業鏈價值鏈控制力和話語權的角力場;發展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,則有助于我國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。
2、與數、智、信息科技深度融合的“新實體經濟”
在十九大報告相關論述中,并非籠而統之地強調實體經濟的極端重要性,而是進一步揭示了未來5年,我們將要發展一種什么樣的實體經濟?
譬如在解讀何謂“制造強國”時,報告就指出:“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,推動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相融合。”由此可見,我們所期許的,“能夠承載經濟著力點”的實體經濟,是一種將數智信息科技和傳統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“新實體經濟”。
李建軍分析:“十四五”期間,實體經濟在和新技術結合的過程中,將碰撞出很多火花。比如工業互聯網對傳統實業的改造,帶來的影響就是巨大的,勢必會淘汰一批落后產能,但那些與工業自動化、工業互聯網深入結合的產能,將會被重點挖掘。包括整個工業企業的SaaS系統、數據上云……而且,這些都是能夠從底層提升工業化效率的經濟形態,對于投資、創業都是利好。
實體經濟的數字化,對人才的需求同樣是巨大的。
“以前只需要生產線‘基礎工人’,未來需要的則是‘數字化工人’。這些高級藍領,不僅要對工業互聯網有一定的理解認知,還要熟練掌握物聯網、傳感器等相關新技術應用……由此,不管是整個市場的需求,還是對人才的更新換代,‘新’實體經濟都蘊含著豐富的創富機會。”李建軍舉例。
葉衛剛表示: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誰,從高科技方面遏制中國的發展,都是不變的,所以,中國未來的發展,高科技環節必須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。另外,供應鏈環節也是一樣,低端產能都轉移出去無所謂,但制造業核心環節要留在中國。所以,對于那些依賴進口的高端制造業而言,亟需盡快找到自主可控的國產替代途徑。
“以上是國家早在兩三年前就看得很清楚的趨勢,這次借‘十四五’規劃又強調了一下,也透露出很多政策紅利。尤其對達泰這種從創立第一天就以技術創新為主導的基金,更是利好。因為我們投資的企業,本身就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,投資企業的合作伙伴也大多來自實體經濟。”葉衛剛說:“但對于習慣靠虛擬經濟賺快錢的基金而言,將是一個重新學習的過程。
對于每一次的政策風向標,投資人的反應都是迅速的。早在一年前,資本市場很多從來不做硬科技、不投實體的基金,就開始轉變賽道,從模式創新向硬科技方向轉型。但正如葉衛剛所言,這類基金因為缺少產業積累,也沒有投資硬科技項目的經驗,未來的轉型之路,勢必漫長而艱難。
葉衛剛提醒,未來幾年二級市場和to IPO階段的硬科技投資,像芯片、生物醫藥的泡沫應該會很大。“因為有人還想著像10年前追逐風口上的‘豬’那樣——先把錢賺過來,再找一些相對成熟的to IPO項目投資……但股權投資領域,‘賺快錢’的思路本身就是歪的。”
3、未來5年,數字化轉型將成企業戰略的必選題
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,總體規模從“十三五”初的11萬億元,增長到2019年的35.8萬億元,占GDP比重36.2%,對GDP的貢獻率為67.7%。而伴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,我國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交易額均居世界首位,大數據、云計算、物聯網、人工智能等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發展,催生出大量新業態新模式。
另外,在網絡建設方面,“十三五”以來,我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,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一半以上,5G商用邁出堅實步伐,已累計開通5G基站69萬個,連接用戶數超過1.6億。數字化將促實體經濟更好發展。
由此可見,從“十二五”到“十三五”,從信息化到網絡經濟,經過這十年的發展,我國數字化快速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。
展望“十四五”,數字化轉型的趨勢又是什么?
富國富民(北京)資本董事長王世渝向《中外管理》談道:“十四五”規劃所講的“企業數字化轉型”,是基于5G時代后數字技術更加復雜,取得了更大進步,加上5G大帶寬、大容量、低延時的特征,給原來數字化技術帶來了巨大空間,進而創造出的更多企業數字化轉型機會……更重要的是,這種數字化轉型機會,不僅是傳統企業的,也是互聯網企業的。”
“比如目前大量門戶網站,就需要通過對復雜數字技術的應用,比如:大數據,云計算、物聯網、AI等,從普通互聯網公司,向更高效、更高科技含量的數字化公司轉型。”王世渝解釋:“所以,2020年作為‘十四五’的規劃之年,數字化轉型不再是戰略選擇題,而將成為企業戰略的必選題,這點對所有企業適用。未來5年,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快與慢,成與敗,關乎的不僅僅是增長速率的問題,還決定著能否生存下去。”
葉衛剛補充:新的歷史時期,國家在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前,首先要把競爭環境搞得公平一點。不管是阿里巴巴,還是螞蟻金服,互聯網公司該交的稅也得交,只有讓互聯網企業交的稅跟實體商場一樣了,整個產業體系數字化才能實現。“過去幾年,電商企業基本不交稅,而實體經濟企業,房租高、稅收高,員工成本也高,政策一直在向虛擬經濟傾斜,兩者面臨著不公平的競爭環境。”
4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,需要補足短板、鍛造長版
在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部署中,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擺在了重要位置。
回顧“十三五”期間,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,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。其中,2019年,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11.5%,比2014年提高3.9個百分點,已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。
李建軍表示,“十四五”時期,國家會大力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,企業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尋找機會:
一方面,重點布局包括芯片、集成電路等面臨“卡脖子”問題的關鍵領域;另一方面,重點聚焦新興信息產業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高端裝備制造業等代表產業鏈升級大方向的重點領域。具體如下:
一是新材料。包括特種功能材料和高性能復合材料,這是兩個重要方向。因為新材料的應用,會對相關產業造成特別大的影響,甚至帶來顛覆性影響。比如新材料在電池里的應用,新材料在手機上的應用,新材料在服裝上的應用等。中國像石墨烯、超導等重要新材料研發尚處于實驗室階段。在很多新興產業方面,中國和國外的差別并不是沒有,而是尚未形成產業化。
二是新能源。包括核能、太陽能、風能、生物質能等。尤其在新能源汽車方面,中國在汽車工業方面已經落后國外很多代,好不容易在新能源汽車上有了一次彎道超車的機會,國家一定會不惜余力地大力推廣。畢竟在新能源技術上,中國不比國外差。
三是新興信息產業。包括高性能的集成電路和高端軟件。比如手機里最常用的 CAD軟件,中國僅限于芯片設計環節,缺少類似CAD這樣底層的東西,這意味著,所有高端軟件中國大多無法自己生產。所以,解決這方面應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,必將是未來一個大方向。
四是高端制造。重點是航空航天、海洋工程設備和高端智能裝備。這些也是我國相對“卡脖子”的領域,但前景也是非常好的。
葉衛剛提醒,解決技術“卡脖子”問題時,不能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,即不能從以前那種完全市場化的做法,一下子回到計劃經濟那種以“舉國體制”來抵制“卡脖子”問題。
“因為,中國能被‘卡脖子’的環節太多了,上上下下能找出幾千個點來,這是整個工業基礎的問題,與其把錢集中起來給幾個效率低的巨無霸企業,不如把錢分散,通過市場化投資機構的力量,去扶持大量創新型企業,讓一個個小企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。也就是,要靠市場的手段去培育一個生態系統。”

 公眾號
公眾號
 小程序
小程序
 微信咨詢
微信咨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