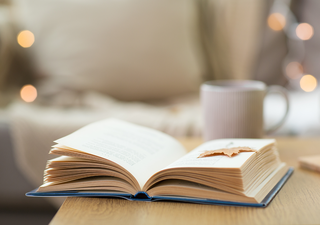隨著劉女士遭遇的曝光,有網友感嘆:“家暴都逼得人跳樓了,還扯什么調解?”一些“過來人”更是唏噓:“鬼知道離婚有多難!”
河南商丘的劉女士很不幸。
結婚后,她遭受過多次家暴。2019年8月,被丈夫竇某某拖拽頭發暴打后,她從二樓跳下,全身9處骨折,雙下肢截癱。今年6月,劉女士向當地法院提起離婚訴訟;一個月后,法院以“雙方意見不統一”為由要求調解、不作判決。
對飽受家暴之苦的劉女士來說,離婚,比想象中要困難得多。
調解
隨著劉女士遭遇的曝光,有網友感嘆:“家暴都逼得人跳樓了,還扯什么調解?”一些“過來人”更是唏噓:“鬼知道離婚有多難!”
調解,是我國《婚姻法》明確規定的離婚訴訟法定程序。它的本意是在當事雙方離婚前,使其充分考慮離婚對家庭、子女等的負面影響,避免草率離婚。
在司法實踐中,當事人第一次起訴離婚,法院通常不會判離;如果沒有新的事實和理由,原告只能在6個月后向人民法院再次提起訴訟。而在第二次起訴離婚過程中,調解還是必經程序。
調解必須,但不能成為離婚的阻卻事由。
《婚姻法》直接指出,“實施家庭暴力”的情形,調解無效的,應準予離婚。也就是說,類似劉女士與竇某某這樣的“家暴離婚案”,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,法院應當直接準予離婚,容不得半點含糊。
而在本次事件中,當地法院還給出了另一個理由——竇某某因毆打劉女士被刑事羈押,離婚訴訟(民事案件)要等刑事案件有結果后再一起判決。
對此,多位法律從業者告訴島叔,劉女士離婚訴訟案作為獨立案件,不必適用“先刑后民”的程序,更不應跟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綁在一起。
被家暴致殘,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身心巨創,另一方面還要接受施暴者作為自己法律意義上的丈夫。這本身對婚姻二字就是莫大的諷刺。
捆綁
近年來,與“離婚”捆綁在一起的東西有很多。
比如孩子。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,每年高考結束,似乎就有一波“離婚潮”。據某地民政局統計,2009年以來,每年高考結束后20天內辦理離婚登記者均要比高考前20天的辦理者增多數倍。申請離婚者中,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約占七成。
比如傳統。老話講,“寧拆十座廟,不毀一樁婚”。只要當事雙方有一絲遲疑,各種勸和力量就會不斷“施救”。在某地司法所蹲點調研時,島叔眼見一起離婚案被司法所前后調解17次,但到最后,雙方還是一拍兩散。
比如政策。前些年司法領域強調“能動司法”、“大調解”,某些地方曲解了法院調解的本意,爭先恐后開展“零判決競賽”活動,使不少離婚案在“調解優先”的政策導向下被異化為“以判壓調”“以拖促調”。這既悖離了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基本要求,也損害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。
比如“善意”。某地“最美紅娘”典型宣傳中有這樣一個案例:“9年來,婚姻登記處的某某以‘打印機損壞’‘網絡故障’等善意謊言,挽救了500多樁瀕臨破裂的婚姻。”
很多國人認可“床頭吵架床尾和,夫妻沒有隔夜仇”的老理。想離婚?您先冷靜一天,要不就冷靜一年,離婚的念頭也就消失了。
數字
電視劇《新結婚時代》中,顧小西媽媽有一段臺詞:
“結婚不只是兩個人的事,你嫁給了他,就等于嫁給了他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。你們倆的結合就是兩個家庭的結合,他娶了你,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,包括你的社會關系、你的父母。”
婚姻的復雜,讓不少人慨嘆離婚好難。而不斷飆升的離婚數據又呈現出現實的另一面——
公開數據顯示,自2003年起,我國離婚率連續15年上漲,2017年已達3.2‰;而自2013年起,我國的結婚對數開始逐年下降,2013年為1346.9萬對,2018年降至1013.9萬對。
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司長王金華介紹,2019年全國婚姻登記機關共辦理結婚登記947.1萬對,離婚登記415.4萬對。
2015-2019年中國結婚、離婚登記情況

資料來源:統計局、智研咨詢整理
2015-2019年中國粗離婚率走勢

資料來源:統計局、智研咨詢整理
錢鐘書先生有一句形容婚姻的名言:“婚姻是一座圍城。城里的人想出來,城外的人想進去”。從現實情況看,出城的人正不斷增加,進城的人卻在減少。
民政部調研數據顯示,當代人離婚通常與“感情基礎差、父母干涉多、外界誘惑大、自我意識強、婚姻觀念‘潮’”等因素相關。
相比“婚姻不易,且行且珍惜”的信條,不少年輕人選擇了“好聚好散”,甚至有人在婚前婚后都奉行“AA制”,只要沒孩子,所有事情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
冷靜
如今,愈來愈高的離婚率給制度設計敲響了警鐘。
其中最引人關注的,就是《民法典》對“離婚冷靜期”的設置。經由“冷靜期”,沖動、輕率、猶豫型離婚在某種程度上被遏制,“可離可不離”的婚姻關系也有了緩和余地。這一點,符合中國“保障離婚自由、防止輕率離婚”的離婚立法指導思想。
而就本案來說,劉女士的遭遇和“離婚冷靜期”無關。“冷靜期”適用范圍僅限于民政機關協議離婚,不適用訴訟離婚。
我們常掛在嘴邊的婚姻自由,其實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兩方面。前者易懂,后者則意味著當事人在感情確已破裂的情況下,享有隨時提起離婚訴訟的權利。
劉女士一案的癥結,恰恰在于離婚自由的受阻。據當地法院工作人員透露,該案訴前調解現已結束,正在進一步審理過程中;當地多部門也已成立聯合調查組,“依法依據還事實一個真相”。
可是,為什么非要“不曝光不解決,一曝光忙著解決”呢?離婚訴訟、離婚自由,結合其具體情形,本不該成為“鬼才知道有多難”的事情。
劉女士一案的發酵,更不應止步于未婚人士眼中的恐婚教材,而應成為司法機關審理相關案件的現實參考。

 公眾號
公眾號
 小程序
小程序
 微信咨詢
微信咨詢